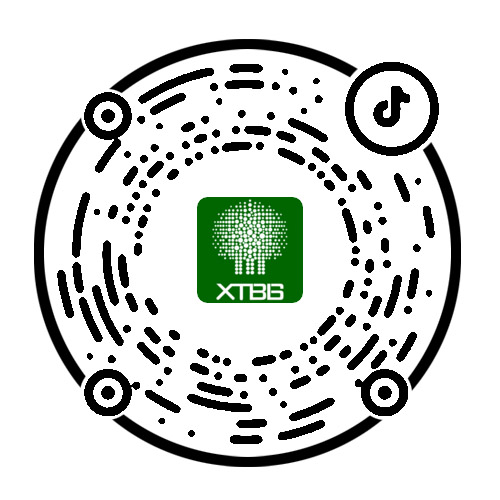中國科學(xué)報:生物學(xué)生辨識不清動(dòng)植物?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被忽視

■本報記者 袁一雪
前不久,中國科學(xué)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研究人員,在《科學(xué)》雜志發(fā)表了一篇題為《一種跳蛛的長(cháng)期哺乳行為》的研究論文。非哺乳動(dòng)物也能通過(guò)哺乳養育后代,一時(shí)間“蜘蛛奶”引發(fā)諸多熱議。其中有一位專(zhuān)家在朋友圈發(fā)表言論:“版納植物園的工作還說(shuō)明,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(行為學(xué)、生態(tài)學(xué))一樣可以有漂亮的工作發(fā)表在國際頂級刊物,并不只是分子、微觀(guān)的。”
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邊緣化,是一個(gè)老話(huà)題,也并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。早在1997年,《科學(xué)》雜志發(fā)表了題為《美國大學(xué)生命科學(xué)院系重組》的文章。事件的起因便是美國越來(lái)越多的研究人員傾向于微觀(guān),因為這樣更容易獲得經(jīng)費等資源,更容易作出成績(jì)。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領(lǐng)域則受到擠壓。
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在中國經(jīng)歷了怎樣的發(fā)展?現狀及前景如何?近日,《中國科學(xué)報》采訪(fǎng)了相關(guān)專(zhuān)家。
2004年,《中國植物志》最后一冊終于正式出版。這部80卷126冊堪稱(chēng)世界最大的植物志由四代植物分類(lèi)學(xué)家歷時(shí)45年編纂完成。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張憲春是312位作者之一,也是最后一冊的完成者。從1989年碩士畢業(yè)開(kāi)始就加入了《中國植物志》寫(xiě)作工作。他說(shuō),現在國內真正還堅守在植物分類(lèi)學(xué)研究的學(xué)者已經(jīng)所剩無(wú)幾:年紀較大的老科學(xué)家或故去,或不再繼續工作,而一批優(yōu)秀的分類(lèi)學(xué)家則轉到微觀(guān)進(jìn)化研究領(lǐng)域。
雖然一直堅守植物分類(lèi)學(xué)研究,但是張憲春帶領(lǐng)的研究組卻包括三個(gè)不同研究方向:蕨類(lèi)、苔蘚與化石植物,每年研究所的資源配置卻和其他單獨研究方向的研究組一樣,如此一來(lái),每個(gè)研究方向就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資源配置,研究生招生名額每年也只有1名博士和1名碩士,雖然研究組有兩個(gè)博士生導師。
“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在現在的學(xué)科發(fā)展中是有些尷尬的。”張憲春無(wú)奈地坦言。這樣的尷尬主要來(lái)自科學(xué)研究的評價(jià)標準,分類(lèi)評價(jià)又很難被貫徹執行。在微觀(guān)分子生物學(xué)新發(fā)現層出不窮的今天,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相關(guān)的學(xué)科逐步被邊緣化,師傅帶徒弟、十年方能出師的師承方式也已式微。
國際研究趨勢的改變
回顧歷史,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也曾繁榮一時(shí)。新中國成立后,百廢待興。一批又一批學(xué)子被公派出國,再回國學(xué)以致用。因為歐洲的分類(lèi)學(xué)起源比較早,1753年時(shí),瑞典人林奈在歐洲就出版了世界性的《植物種植》。我國卻直到1905年才開(kāi)始采集植物標本。所以去歐洲學(xué)習生物學(xué)的學(xué)子們多以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中的生物分類(lèi)學(xué)為主。
學(xué)成歸來(lái)后,因為當時(shí)科研體系尚未完整建立,加上受到科研儀器的制約,所以國內生物學(xué)的起源也都由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起始,比如,中科院動(dòng)物研究所的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就由歸國的老科學(xué)家們一手建立。那時(shí),高校生命科學(xué)教學(xué)的基本內容也是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。
然而,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在我國繁榮并未太久,上世紀50~70年代,國際分子生物學(xué)的快速發(fā)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,不僅該領(lǐng)域的科學(xué)家更容易作出成果、更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等國際科學(xué)大獎,而且與分子生物學(xué)相關(guān)的以細胞、基因為主要對象的生物和醫學(xué)產(chǎn)業(yè)也獲得極大發(fā)展,創(chuàng )造出令人矚目的經(jīng)濟利益。“歐洲生物學(xué)研究將重點(diǎn)從宏觀(guān)轉移到微觀(guān),還因為歐洲植物種類(lèi)不到我國的二分之一,研究時(shí)間又長(cháng),所以幾乎已經(jīng)研究透徹。”張憲春告訴《中國科學(xué)報》。
國際科研趨勢的轉變也漸漸影響國內的研究,而且之后出國留學(xué)的人員多以微觀(guān)分子學(xué)為主,歸來(lái)后的研究重點(diǎn)也逐漸傾斜。但是我國的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發(fā)展卻并不充分。盡管《中國植物志》已經(jīng)出版,但很多植物大量標本長(cháng)期無(wú)人鑒定,錯誤鑒定的標本還沒(méi)有得到糾正,新的物種也不斷被發(fā)現和不能得到描述和發(fā)表。
如今,在為數不多的植物分類(lèi)學(xué)研究人員中,張憲春是全國唯一可以招收博士生研究蕨類(lèi)種群的導師。“我國蕨類(lèi)分類(lèi)學(xué)做得還比較好,但種子植物中一些比較大的類(lèi)群,比如杜鵑類(lèi)、薔薇類(lèi)的研究人員中,已經(jīng)見(jiàn)不到中堅力量。”張憲春說(shuō)。
馬上面臨斷代的不只是植物分類(lèi)學(xué),動(dòng)物分類(lèi)學(xué)也面臨著(zhù)同樣的境況,甚至在中科院動(dòng)物研究所標本館中,很多昆蟲(chóng)標本依然未標明門(mén)類(lèi)。中科院動(dòng)物研究所研究員王德華在接受《中國科學(xué)報》采訪(fǎng)時(shí)說(shuō):“現下,盡管動(dòng)物分類(lèi)學(xué)研究中,無(wú)脊椎動(dòng)物和脊椎動(dòng)物的分類(lèi)學(xué)研究都有學(xué)者在做,但都存在人才匱乏的問(wèn)題。就動(dòng)物研究所的獸類(lèi)和鳥(niǎo)類(lèi)分類(lèi)學(xué)而言,只有兩個(gè)課題組在做。而且,他們在關(guān)注分類(lèi)學(xué)的同時(shí),也不得不拓展新的研究領(lǐng)域。”
科研評價(jià)體系的導向
除了研究趨勢的改變,國內引入了國際的科學(xué)評價(jià)體系SCI也是令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不斷沒(méi)落的原因之一。每年發(fā)表論文的數量,影響因子高低等硬性的考核標準橫亙在每位科研人員的研究道路上。若要通過(guò)考核就要迎合國際研究熱點(diǎn)。如此一來(lái),微觀(guān)分析、驗證其他科學(xué)家的實(shí)驗或者發(fā)現的新的方法,令微觀(guān)領(lǐng)域研究人員完全可以完成論文的硬性指標。但這些對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的研究人員來(lái)說(shuō)卻并不容易。達不到考核標準,一些做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研究的科研人員很難申請高級職稱(chēng),甚至課題組都面臨被解散的命運。看不到前路,也令不少人轉到其他領(lǐng)域。
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受到波及的不僅是科研領(lǐng)域,一些高校生物專(zhuān)業(yè)在本科階段簡(jiǎn)化甚至取消了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。一直關(guān)注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發(fā)展的復旦大學(xué)生命科學(xué)學(xué)院遺傳與遺傳工程系遺傳學(xué)教授喬守怡告訴《中國科學(xué)報》:“一般生物學(xué)相關(guān)專(zhuān)業(yè)在本科階段會(huì )開(kāi)設動(dòng)物學(xué)與植物學(xué)的基礎課,但現在的教學(xué)體系設置,逐漸趨向減少了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課程的設置,弱化了對生物個(gè)體,群體和生態(tài)領(lǐng)域知識的認知體系,讓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變得十分薄弱。這對宏觀(guān)領(lǐng)域人才培養影響很大。”
北京大學(xué)生命科學(xué)學(xué)院副院長(cháng)、教育部高等學(xué)校生物科學(xué)與工程指導委員會(huì )副主任許崇任在2007年一個(gè)論壇主題發(fā)言中介紹:依據北京大學(xué)1959年的教學(xué)計劃,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課程占絕大部分,但2007年北京大學(xué)的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的課程只占1959年教學(xué)計劃學(xué)時(shí)數的1/3。
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是基石
“生物學(xué)的每個(gè)層次都是不可替代的,每個(gè)層次有每個(gè)層次的問(wèn)題。我們現在科研要進(jìn)軍微觀(guān),但同樣不能忽略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,人與自然環(huán)境是密不可分的。我們不能一邊擁有敲掉腫瘤基因的技術(shù),一邊卻生活在充滿(mǎn)污染的環(huán)境中。脫離宏觀(guān)環(huán)境談人類(lèi)健康是很矛盾的。”王德華說(shuō)。
而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本身也與工業(yè)、農業(yè)、科教以及外交和外貿有著(zhù)密切關(guān)系。從這一點(diǎn)看,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是生物學(xué)研究的基礎,只有了解生物個(gè)體和群體的關(guān)系,清楚它們與人類(lèi)的關(guān)系,才能提出需要解決的問(wèn)題,分子生物學(xué)是詮釋整體生物問(wèn)題的一個(gè)層次和手段。宏觀(guān)與微觀(guān)兩個(gè)層面的研究,研究者可以專(zhuān)攻一個(gè)層面,但是生物科學(xué)的研究與發(fā)展需要一個(gè)整體系統,重視宏觀(guān)生物的研究和人才培養,是生物學(xué)科發(fā)展的基本環(huán)節。一旦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發(fā)生錯誤,那么后續的研究也將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。
張憲春就曾在分類(lèi)學(xué)研究中發(fā)現,在上世紀80年代被科學(xué)家找到的含有治療阿爾茨海默病成分的蛇足石杉,其物種分類(lèi)尚存在問(wèn)題。他依據形態(tài)特征和葉綠體基因信息,證明我國的藥用蛇足石杉來(lái)自?xún)蓚€(gè)截然不同的物種。在分類(lèi)學(xué)中,蛇足石杉中的有效成分石杉堿甲含量并不高,而另一種被忽視的長(cháng)柄石杉中卻含有較高含量的石杉堿甲。“之前植物志中的記載也有誤,所以也需要糾正。而這些工作都要分類(lèi)學(xué)家完成。”張憲春說(shuō)。
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忽視之弊
“不識生物真面目,只緣身在分子中”是喬守怡在幾年前提出的,他認為忽視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是“舍本求末”。
但現在,這種現象卻愈演愈烈。王德華舉了個(gè)例子,比如要對某種動(dòng)物進(jìn)行研究時(shí),有些研究者可能沒(méi)有親自到野外去采樣,對于樣品的整體生物學(xué)特性沒(méi)有第一手資料。但這并不影響論文寫(xiě)作,因為他們會(huì )根據公司或實(shí)驗室的分析儀器測定的分子數據完成論文。看似研究工作進(jìn)行得不錯,但從始至終,他們都不知道研究對象生活在何處,生活習性如何,甚至可能都不清楚它的樣貌。對此,張憲春也坦言,分子研究中的研究對象標本留存確實(shí)存在漏洞。因為研究者關(guān)注的只是分子,但如果有同行要求重復或繼續此項研究,其標本還能不能找到都是問(wèn)題。
更令喬守怡擔憂(yōu)的是,如今生物類(lèi)專(zhuān)業(yè)科班出身的學(xué)生,在野外動(dòng)植物的認知能力遠不如老一輩學(xué)者。“如果再不關(guān)注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的傳承,那么可能連身邊的動(dòng)植物都辨識不清,缺乏對生物資源的基本認知,一旦出現斷代是很難恢復的。”
張憲春同樣感到擔憂(yōu),他唯有將蕨類(lèi)種群專(zhuān)業(yè)教授給更多適合做分類(lèi)學(xué)的人,讓他們繼續堅守。不過(guò),令他感到欣慰的是,來(lái)自化學(xué)、航空等其他專(zhuān)業(yè)報考其研究生的大有人在,他們懷著(zhù)對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最單純的熱情。但對每一位前來(lái)報考的學(xué)生,張憲春每次都鄭重告知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的現狀,讓他們考慮清楚前路。“我認為國家還是應該保留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的隊伍,因為我國地大物博,還有很多植物與動(dòng)物需要作分類(lèi)學(xué)研究,也只有將我國的資源摸清楚,才能進(jìn)一步作微觀(guān)研究。”張憲春說(shuō)。
建設人才隊伍,喬守怡也認為十分必要,因為我國特有資源的認識、利用和保護需要專(zhuān)門(mén)的人才,沒(méi)有這批人的傳承就無(wú)從談起資源充分利用。而且,當科學(xué)家在追求高深微觀(guān)前沿的時(shí)候,更要研究生物的本源,才能更了解自己研究的意義何在。更重要的是,“科學(xué)家不是工匠,不只是簡(jiǎn)單地操作機器完成論文就可以。我們更需要通過(guò)宏觀(guān)生物學(xué),尋找存在體系中的問(wèn)題才能進(jìn)行研究。如果我們只會(huì )做微觀(guān)研究,卻連辨識植物的人才都找不到,又從哪里尋找微觀(guān)研究的對象呢?只有擁有宏觀(guān)知識的底蘊才能深入挖掘生物資源對人的重要作用”。